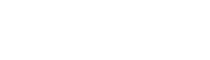“毕加索的吉他,1912-1914”主题展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,从2月13日持续到6月6日。正因为唤起了这些思考,这把纸板吉他和后来创作的金属翻版(也是展品之一)成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之一。

《亚威农的少女》
1912年的毕加索待在巴黎,想着:好了,下一步要做什么?
五年前他画了一幅重磅作品《亚威农的少女》。外界大惊失措,连他的朋友们也不多做评价。人们的大惊小怪更加激励了毕加索,他用同一个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变体:油画中裸体女人的肢体棱角分明,手肘尖锐,皮肤呈木棕色。身体的棱角如斧切般呈现多维度,嵌在平面化的空间。
他的作品改变了艺术史。他把古典美术作品中温和、理想化的裸体人像改造成危险、带着防卫性的女人。他使艺术变得既是一种乐趣,又是一大问题。同时他并未改变绘画基础,人体依然是完整的,并非抽象。此时他的作品仍是现实世界的反映,尚未创造出一个自有一派律法的异象世界。

《瓶子,吉他和管子》(Bottle, Guitar, and Pipe
还有新花样可以探索出来,毕加索或许会自问在这条路上到底愿意走多远。
事实证明,他走得很远,正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举办的主题展“毕加索的吉他,1912-1914”所展现。展品一共有70件:四处借来的油画、素描、拼贴画及两座雕塑,其中一件雕塑作品在毕加索过世后被搬出他的工作室,此为首次以完整形态跟公众见面。
单个看每件作品都很迷人;作为整体来看,更是对一场短暂而深刻的革命的记录,很多现代艺术中最具挑战意味的理念便是由这场革命启发的。
在1912年之前,毕加索受到了朋友乔治・布拉克的灵感启发,把注意力从人像转移到静物上。用布拉克的原话来说,他们二人如“同一条绳索上的登山者”一样,一起开创了立体主义流派。
立体主义在初期与其说是一种风格(虽然后来显然成了一种流派)不如说是一种重新思考艺术在当今世界处于何种位置的方式。对20世纪初的一些艺术家来说,艺术的地位很不确定。摄影的纪实镜头使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变得多余。与此同时,随着社会、科技、宗教、政治等领域的发展,“真实”的定义再明显不过。

《吉他,乐谱和玻璃杯》(Guitar, Sheet Music, and Glass1912年
哪种类型的艺术才能立足于变化中的时代呢?能够反思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艺术才可以。这样的艺术既可以渗入到日常生活(当时盛行的学院派做不到这点),还能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:不断求变、改造传统、制造新意。
这类思考便是毕加索和布拉克在创办立体主义初期所进行的。对于他们需要应对的复杂环境而言,他们没有采取捷径、或是半路迷失、或是失去势头,属实是个奇迹。“首要的是我们都很专注。”布拉克后来写道。这种专注可以从MoMA的这个展览窥见一斑,布拉克在这个展览中虽隐形,却又无处不在。
有种显而易见的手法是通过精简作品中静物的种类使风格更简约:酒杯、玻璃瓶、咖啡杯以及乐器――小提琴和吉他――主要由这几类物件组合而成。它们在小酒吧和咖啡馆中很常见,艺术家们喜欢在冷天从工作室聚集到这些地方取暖。由此看来立体主义已然具备了某种现实元素,取材自部分的现实生活。
展出的毕加索的早期作品中,他仍固守其作为画家的身份,这个身份在传统的艺术等级中位居高位,而立体主义很快就要打破这个等级了。

《吉他》(Guitar使用的材料有报纸、壁纸和粉笔
在《瓶子,吉他和管子》(Bottle, Guitar, and Pipe)中,物件看起来像是被切开,一层层歪歪斜斜地叠在平面上。这幅具有高密度拼贴画特征的作品,有点像剪切、粘贴、组合而成的设计,堆积起来的不同平面之间由淡淡的阴影过渡;只不过阴影和平面都是颜料刷上去的。这个立体感的作品不过是一幅布面油画。
毕加索很快又扩展了他常用的材料。1912年秋季所作的《吉他,乐谱和玻璃杯》(Guitar, Sheet Music, and Glass)由剪报、活页乐谱和仿木纹纸拼贴而成。仿木纹纸面上的花纹是手绘的,但不一定是毕加索本人绘制。
所署日期为1913年3月31日的《吉他》(Guitar)是一幅极为前卫的作品,完全没有使用颜料。在此,绘画通过人为地重现自然写实主义的印记了无影踪。取而代之的是立体主义的真实原则:在一层新奇的物件上黏上另一层物件。吉他的塑性如同附有幽灵般,看似被切块,却无容积无深度可言,也不必指向外在现实中具体的真实存在。从作品中不难发现,毕加索喜欢形状诡异的拼贴多于连接紧密、流畅的结构。
一个世纪后的今天,很难体会当时这样的作品对一些人来说有多令人不安――造成的坏影响比年轻人的狂欢喧闹更让人不堪忍受。这些作品如同一记耳光,让美学、礼法和理想主义齐齐挨了巴掌,成了欧洲文明每况愈下的明证。
很多人为此触怒。巴黎的艺术报刊《巴黎之夜》(Les Soirées de Paris )刊登了一张毕加索用纸板和琴弦制作的吉他雕塑作品的照片,愤怒的读者来信汹涌而至,人们甚至因此取消对该报的订阅。

用纸板做的吉他雕塑
而引起争议的吉他纸雕正是本次MOMA展览的主要展品。毕加索于1912年秋冬季节在巴黎完成了这件作品。大小同现实吉他,却脆弱易坏地使人心疼,且没法用来弹奏。它体现了立体主义流派提出的诸多美学问题:什么是真实?为什么有些版本的“真实”会比其它版本的更好?什么是“高端艺术”,什么是“低端艺术”?又是什么让“持久的”比“短暂的”更有价值?又是什么决定一个物件是艺术品,或者一个理念不是艺术?
正因为唤起了这些思考,这把纸板吉他和后来创作的金属翻版(也是展品之一)成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之一。
毕加索自己也很珍视这件作品。1912年他给它拍了些照片,几年之后把它拆开,再打包收起来。他再也没有公开展示过《吉他》,虽然多次有人要求。1973年毕加索过世前,把它留给了MOMA。
2005年,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艺术史教授Christine Poggi询问MoMA这件纸雕是否有部件缺失,她从展览中观察到原先作为吉他“底座”的圆形纸片不见了。于是博物馆从仓库中进行了一番大搜查,终于找到了这块“底座”,归回原位。于是,展现完整吉他纸雕更成为举办此次展览的必要缘由。
策划人――绘画和雕塑部门的主任Anne Umland和策展助理Blair Hartzell――对这项计划非常满意。他们把一批精妙又罕见的作品汇集在一起,生动直接地展现给我们看,毕加索在作为分水岭的这两年中拓展自己到了何种境界。

1913年的拼贴画《头部》Head
他这么做可不容易。毕加索是天生的人物画家,坚守布拉克“只画静物”的准则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,而事实上他也并未完全照规矩来。“人体”不断出现在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中,哪怕只是将吉他变形成躯干、小提琴变形成头部。
尽管已经走得够远,毕加索自身还是有限制。他从未因“描绘”的画法彻底投入到完全抽象创作中。1913年的拼贴画《头部》(Head)是他离抽象画最近的一次(展出的这幅作品由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立现代博物馆提供)。如果他不在白色圆锥体上用铅笔点上那只眼睛的话,这就是一幅完全意义上的抽象画了――不知这只眼睛是不是最后一刻才点上去的?
至于立体主义,至少是早期的立体主义,因一战的硝烟而暂停。而战争结束后,没人再想听关于“现实的不稳定性”、“价值观及美学的相对性”这类的探讨。但不能说立体主义已死,作为一种流派,它最终迎来了繁荣,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1914年之后的毕加索又开始了新的篇章――或者说重捡以前的热情所在。他回到了人像的创作,类似安格尔肖像画中身着希腊式长袍的少女,或是鲁本斯画的肉感裸女。此时的毕加索似乎遗忘了自己多年前曾创作过充满情欲的战士画像,抑或震惊世界的拼贴作品――这些大胆又精致、带来了立体主义革命的拼贴作品,来自毕加索最出色的时期。(周恩)

《亚威农的少女》
1912年的毕加索待在巴黎,想着:好了,下一步要做什么?
五年前他画了一幅重磅作品《亚威农的少女》。外界大惊失措,连他的朋友们也不多做评价。人们的大惊小怪更加激励了毕加索,他用同一个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的变体:油画中裸体女人的肢体棱角分明,手肘尖锐,皮肤呈木棕色。身体的棱角如斧切般呈现多维度,嵌在平面化的空间。
他的作品改变了艺术史。他把古典美术作品中温和、理想化的裸体人像改造成危险、带着防卫性的女人。他使艺术变得既是一种乐趣,又是一大问题。同时他并未改变绘画基础,人体依然是完整的,并非抽象。此时他的作品仍是现实世界的反映,尚未创造出一个自有一派律法的异象世界。

《瓶子,吉他和管子》(Bottle, Guitar, and Pipe
还有新花样可以探索出来,毕加索或许会自问在这条路上到底愿意走多远。
事实证明,他走得很远,正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举办的主题展“毕加索的吉他,1912-1914”所展现。展品一共有70件:四处借来的油画、素描、拼贴画及两座雕塑,其中一件雕塑作品在毕加索过世后被搬出他的工作室,此为首次以完整形态跟公众见面。
单个看每件作品都很迷人;作为整体来看,更是对一场短暂而深刻的革命的记录,很多现代艺术中最具挑战意味的理念便是由这场革命启发的。
在1912年之前,毕加索受到了朋友乔治・布拉克的灵感启发,把注意力从人像转移到静物上。用布拉克的原话来说,他们二人如“同一条绳索上的登山者”一样,一起开创了立体主义流派。
立体主义在初期与其说是一种风格(虽然后来显然成了一种流派)不如说是一种重新思考艺术在当今世界处于何种位置的方式。对20世纪初的一些艺术家来说,艺术的地位很不确定。摄影的纪实镜头使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变得多余。与此同时,随着社会、科技、宗教、政治等领域的发展,“真实”的定义再明显不过。

《吉他,乐谱和玻璃杯》(Guitar, Sheet Music, and Glass1912年
哪种类型的艺术才能立足于变化中的时代呢?能够反思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艺术才可以。这样的艺术既可以渗入到日常生活(当时盛行的学院派做不到这点),还能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:不断求变、改造传统、制造新意。
这类思考便是毕加索和布拉克在创办立体主义初期所进行的。对于他们需要应对的复杂环境而言,他们没有采取捷径、或是半路迷失、或是失去势头,属实是个奇迹。“首要的是我们都很专注。”布拉克后来写道。这种专注可以从MoMA的这个展览窥见一斑,布拉克在这个展览中虽隐形,却又无处不在。
有种显而易见的手法是通过精简作品中静物的种类使风格更简约:酒杯、玻璃瓶、咖啡杯以及乐器――小提琴和吉他――主要由这几类物件组合而成。它们在小酒吧和咖啡馆中很常见,艺术家们喜欢在冷天从工作室聚集到这些地方取暖。由此看来立体主义已然具备了某种现实元素,取材自部分的现实生活。
展出的毕加索的早期作品中,他仍固守其作为画家的身份,这个身份在传统的艺术等级中位居高位,而立体主义很快就要打破这个等级了。

《吉他》(Guitar使用的材料有报纸、壁纸和粉笔
在《瓶子,吉他和管子》(Bottle, Guitar, and Pipe)中,物件看起来像是被切开,一层层歪歪斜斜地叠在平面上。这幅具有高密度拼贴画特征的作品,有点像剪切、粘贴、组合而成的设计,堆积起来的不同平面之间由淡淡的阴影过渡;只不过阴影和平面都是颜料刷上去的。这个立体感的作品不过是一幅布面油画。
毕加索很快又扩展了他常用的材料。1912年秋季所作的《吉他,乐谱和玻璃杯》(Guitar, Sheet Music, and Glass)由剪报、活页乐谱和仿木纹纸拼贴而成。仿木纹纸面上的花纹是手绘的,但不一定是毕加索本人绘制。
所署日期为1913年3月31日的《吉他》(Guitar)是一幅极为前卫的作品,完全没有使用颜料。在此,绘画通过人为地重现自然写实主义的印记了无影踪。取而代之的是立体主义的真实原则:在一层新奇的物件上黏上另一层物件。吉他的塑性如同附有幽灵般,看似被切块,却无容积无深度可言,也不必指向外在现实中具体的真实存在。从作品中不难发现,毕加索喜欢形状诡异的拼贴多于连接紧密、流畅的结构。
一个世纪后的今天,很难体会当时这样的作品对一些人来说有多令人不安――造成的坏影响比年轻人的狂欢喧闹更让人不堪忍受。这些作品如同一记耳光,让美学、礼法和理想主义齐齐挨了巴掌,成了欧洲文明每况愈下的明证。
很多人为此触怒。巴黎的艺术报刊《巴黎之夜》(Les Soirées de Paris )刊登了一张毕加索用纸板和琴弦制作的吉他雕塑作品的照片,愤怒的读者来信汹涌而至,人们甚至因此取消对该报的订阅。

用纸板做的吉他雕塑
而引起争议的吉他纸雕正是本次MOMA展览的主要展品。毕加索于1912年秋冬季节在巴黎完成了这件作品。大小同现实吉他,却脆弱易坏地使人心疼,且没法用来弹奏。它体现了立体主义流派提出的诸多美学问题:什么是真实?为什么有些版本的“真实”会比其它版本的更好?什么是“高端艺术”,什么是“低端艺术”?又是什么让“持久的”比“短暂的”更有价值?又是什么决定一个物件是艺术品,或者一个理念不是艺术?
正因为唤起了这些思考,这把纸板吉他和后来创作的金属翻版(也是展品之一)成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之一。
毕加索自己也很珍视这件作品。1912年他给它拍了些照片,几年之后把它拆开,再打包收起来。他再也没有公开展示过《吉他》,虽然多次有人要求。1973年毕加索过世前,把它留给了MOMA。
2005年,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艺术史教授Christine Poggi询问MoMA这件纸雕是否有部件缺失,她从展览中观察到原先作为吉他“底座”的圆形纸片不见了。于是博物馆从仓库中进行了一番大搜查,终于找到了这块“底座”,归回原位。于是,展现完整吉他纸雕更成为举办此次展览的必要缘由。
策划人――绘画和雕塑部门的主任Anne Umland和策展助理Blair Hartzell――对这项计划非常满意。他们把一批精妙又罕见的作品汇集在一起,生动直接地展现给我们看,毕加索在作为分水岭的这两年中拓展自己到了何种境界。

1913年的拼贴画《头部》Head
他这么做可不容易。毕加索是天生的人物画家,坚守布拉克“只画静物”的准则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,而事实上他也并未完全照规矩来。“人体”不断出现在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中,哪怕只是将吉他变形成躯干、小提琴变形成头部。
尽管已经走得够远,毕加索自身还是有限制。他从未因“描绘”的画法彻底投入到完全抽象创作中。1913年的拼贴画《头部》(Head)是他离抽象画最近的一次(展出的这幅作品由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立现代博物馆提供)。如果他不在白色圆锥体上用铅笔点上那只眼睛的话,这就是一幅完全意义上的抽象画了――不知这只眼睛是不是最后一刻才点上去的?
至于立体主义,至少是早期的立体主义,因一战的硝烟而暂停。而战争结束后,没人再想听关于“现实的不稳定性”、“价值观及美学的相对性”这类的探讨。但不能说立体主义已死,作为一种流派,它最终迎来了繁荣,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1914年之后的毕加索又开始了新的篇章――或者说重捡以前的热情所在。他回到了人像的创作,类似安格尔肖像画中身着希腊式长袍的少女,或是鲁本斯画的肉感裸女。此时的毕加索似乎遗忘了自己多年前曾创作过充满情欲的战士画像,抑或震惊世界的拼贴作品――这些大胆又精致、带来了立体主义革命的拼贴作品,来自毕加索最出色的时期。(周恩)